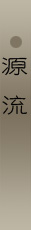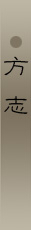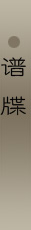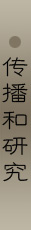刘天一《关于客家渊源于界定的浅见》
关于客家渊源与界定的浅见
刘天一
本人自1984年起,曾先后四次访问福建宁化石壁;还于1991
年参加“梅州市客家历史文化考察团”,一行五人专程到中原一些地方进行考察,现将我在实际工作中的接触与学习,谈些个人对客家渊源与界定的浅见。
客家民系根在中原
众所周知,在我国漫长而复杂的历史长河中,自“秦开五岭”到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藩镇割据、唐末的黄巢起义、两宋的辽金人侵以至宋室南迁,还有元、明、清的朝代更迭,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等,充满了改朝换代和你争我夺的战乱,人祸天灾接踵而来,给中原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因而不得不向南迁徙,为求生存,流离失所,过了长江之后,辗转到江西都阳湖流域,滞留若干年代后,再流徙至赣闽粤三省边区,又经过若干年代的休养生息,与南方某些少数民族(主要是舍、瑶)杂处融合,逐渐形成后来汉民族中的客家、广府及福佬等不同民系。(在江西都阳湖畔筷子巷留居的中原汉民,一部分于明代洪武年间回迁河南信阳的大别山区各县。)我国中原古时历次移民,多数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流徙,这是总的趋势。按罗香林先生的研究,大体分为五个时期。客家人往东南亚谋生,始自宋末元初,明清以后,南渡的更多;自咸丰年间“太平天国”以后,更是大量到了南洋群岛。
客家形成不晚于南宋
客与主,应该是相对而言。中原汉人南迁,作客他乡,这是历史。年深月久,“客而家焉”,或叫“客久在家”,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正常规律。不作什么高深的考证,也颇容易理解!在粤东潮客地区之间,客人称潮人为“福佬,’(“福”字的潮语与客语的“鹤”字同音故客人统称潮人叫“鹤佬”。)而潮人称客人,一向都叫“客人”很少附带一个“家”字,所谓“客家”可能是对民系而言,有如“舍家”、“苗家”之称谓。至于客家这个民系,究竟形成于何时?目前却有多种说法。有人把客家形成时代往前推,似乎越古越光采。但也有人往后推,说是形成于明清。这些推论,本人不敢苟同。
我比较赞同许多专家学者们所主张,有“客家先民”、“先客”、“后客”和“客家后裔”之区分,不能泛泛地一概而论,应有时空界限的阶段性,要避免“以我为主”的自称什么中心,而影响到本民系内部或与其他民系之间的感情。
一个民系的形成,需具备历史上诸多复杂的因素,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一次性完成。客与非客,一般应以某一地域的方言为主要标志。无论是哪一个民系的形成,都离不开人与之间的不断交往或通婚(上层人物还有不同利益的联姻),以及语言文学、风俗习惯、文化传承等的互相影响和融化吸收,否则就不可能成其为某一民系。就我们汉族而言,也是由刘邦成立汉国,逐渐由多个民族的百姓分子,融化而成。
客家研究的先驱罗香林先生,以毕生精力研究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他的著作为我们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但他在三十年代的客观条件下,难免有点大汉族主义情绪,这是容易理解的,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我却完全赞同罗先生所说是在“两宋之间”的论述,最晚也不会晚于南宋。有人认为形成于明清,那就未免过于缺乏常识了。
关于客家先民迁徙赣闽粤边区之后,与当地舍瑶民族的融合,究竟是谁同化谁的问题,我却认为是占多数而又比较先进的客家先民,同化了当地的少数舍瑶民族,而不可能是少数而分散的舍瑶民族同化了客家先民。而在历史事实上,原属舍族的蓝、钟两姓,早已汉化成为汉族中的一员。(目前我们梅州丰顺县潭山镇的凤坪舍族,仅有蓝姓共49户、331人(1987年统计),他们除了对内讲舍话,春节祭祖的图腾崇拜仪式以外,其他许多方面都已基本汉化。梁钊韬先生等曾去潭山舍族村调查过,梁先生曾以古粤语和当地年老舍民对话,基本上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