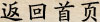闽北定光佛信仰的传人及演变字体显示:大 中 小 创建日期:
主要责任者:黎晓铃
来源:定光古佛与客家民间信仰
摘要:定光古佛与客家民间信仰 闽北定光佛信仰的传人及演变
闽北定光佛信仰的传人及演变
—以建欧定光佛信仰的个案为主要考察对象
黎晓铃
定光古佛是闽西客家人很熟悉并且普遍信仰的神明。他是客家
人在本民系酝酿时期创造出来的守护神,在客家地区产生十分广泛
的影响。其原型是北宋初年活动在汀州的高僧,俗姓郑,名自严,
泉州同安人。于宋初乾德二年(964)驻锡武平县之南安岩,开辟道
场,显示神通,深受民众敬信,死后被神化,成为以闽西为中心的
客家地区民众信仰膜拜的“佛祖”、“古佛”。’
但是,被世人忽略的是,其实,在闽北也有定光佛信仰。且那
里的定光佛不同于闽西,其原型并不是被汀州民众神化的郑自严,
而是长耳定光佛。沙县洞天岩建有老佛庵,庵旁岩石上雕刻着定光
古佛的睡像,俗称“灵岩睡像”。洞天岩还“有长耳佛像,水早祷,
著灵迹。”2可以看到,与闽西不同,闽北的定光古佛的特征是长耳,
, 见谢重光先生《闽台定光佛信仰宗教性质辨析》
2 [明]董其昌《画禅寺随笔》卷3,《笔记小说大观》第12册,页126,江苏广
陵古籍刻印社复印。
而这并不是闽西定光佛所具有的特征。更特别的是,在今天建既一
带所祀奉的定光佛是一位身着红肚兜盘着腿的长耳孩童,据庙祝解
释,这是因为定光佛七岁成佛,因此其形象也是七岁孩童。闽西的
定光佛十一岁出家,在其七岁时,并没有特别的事迹。这更可以证
明,闽北的定光佛与闽西定光佛所指并不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位
长耳定光佛究竟是何许人也?笔者对其进行了一番考证:
《宋高僧传》中记载了一位长耳和尚:
“释行惰。俗性陈.泉州人也.少投北岩院出家.小心受课,
诵念克勤.十三削发.往长乐府戒坛受上品律仪.随众请问.未知
诊旨.辞存师言入浙去.存曰:与汝理定容仪。令彼二人睹相发心.
遂指其耳曰:轮屏幸长,垂瑞扰短,吾为汝伸之.双手平曳,登即
及肩.如是者三,自此长垂,见者举目.后唐天成二年丁亥岁入浙
中.倾城瞻望,檀施纷纷.遂构室于西关高峰,为其宴息,后郁成
大院.惰别无举唱,默默而坐.人问唯笑而止.士女牵其耳交结于
颐下,杭人号长耳和尚。以乾佑三年(950)庚戌岁十一月示疾.动
用如平时.以三月中夜坐终.植越弟子以漆布,今亦存焉.后寄梦
睦州刺史陈荣曰:吾坐下未完.检之元不漆布,重加工焉”3
这位长耳和尚也是泉州人。俗姓陈,名行修。年幼就已经投北
岩院出家。十三岁削发,之后到长乐府学习。接着,又辞别其师存
和尚入浙江。未入浙江之前,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件。其师存和尚
为了给他“理定容仪”,拉长其耳瑞,使其成为长相奇特的长耳和尚。
后唐天成二年,长耳和尚进入浙江,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浙江信
[宋]赞宁: 《宋高僧传》卷第三十, 《汉杭州耳相院行惰传》.
徒为其建造住所于西关高峰,从此定居浙江,成为浙江著名的长耳
和尚。
《闽书》又载:
“杭州西湖南山法相院僧行修,陈氏子.生而异香满室,长耳
垂肩.追七岁尤不言,或曰: ‘哑那?’忽应声曰: ‘不遇作家,徒
撞破湮楼耳.’长游方外,至金陵瓦棺寺祝发受具.参雪峰义存.后
梁开平间(907一910),至四明山中,独棱松下说法,天花纷雨。又
玖坐龙尾岩,结茅为盖,百鸟嘟花飞绕,经岁为常。后唐同光二年
(924),至杭之法相,依石为室,禅定其中.乏水给饮,卓锡岩际,
清泉进出.钱越王以诞辰饭僧,永明禅师告王曰:“长耳和尚,定光
佛应身也.”王趣驾参礼.师默然,但云:‘永明饶舌,,少项,枷跌
而化.久之,益肤革津泽,爪发复长,月必三净.寺僧恐其久而毁
也,乃以发涂骸体.宋咸宁三年,踢号慈大师.”4
可见,行修在杭州修行的具体地点是西湖南山法相院。传说中
行修刚出生的时候就异香满室、长耳垂肩。小时候一直不会说话。
直到七岁的某一天,有人随口问他是否为哑巴时,他忽然告之“不
遇作家,徒撞破湮楼耳”,表明其出家修行的决心。从此长游方外。
其中,在金陵瓦棺寺受具足戒,并拜著名的雪峰义存为师。后梁开
平间,行修进入浙江的四明山说法。说法时发生一些如“天花纷雨气
4 [明1何乔远编撰《闽书》卷之一百三十七, 《方外志》泉州府“杭州西湖
南山法相院僧行修”条,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5年12月第一
版。第钓70页。
[清]徐景熹修施廷枢鲁曾显等纂:《乾隆福州府志》卷之七十一释老也有相
关记载。
198
“ 百鸟吻花飞绕”等神话剧才有的场景。后唐同光二年,行修到了
杭州的法相“依石为室,禅定其中”,“卓锡岩际,清泉进出”,发生
了一系列在密僧身上常发生的神奇事件。钱越王以诞辰饭僧之时,
永明禅师向越王介绍长耳和尚行修,称其是佛教中定光佛的应身。
行修因此受到钱越王的亲自礼拜。因此在浙江声名大震。
《闽书》中所载的长耳和尚行修与《宋高僧传》所记载的释行
修,虽然在细节上有些许不同(如长耳出现的时间不同),但所记载
的事迹基本上是相吻合的,实乃同一个人。其中提到了行修定光佛
的身份。与笔者在闽北所见到的定光佛身份相符。且其中的长耳和
尚七岁突然开口说话。可见七岁在行修一生中是很特别的,被民间
认为是其成佛的标志。还值得注意的是,闽北与信仰长耳定光佛的
浙江,在地域上非常接近。很明显,闽北一带所崇祀的七岁儿童形
象的定光佛是长耳和尚行修,而不是福建人民所熟悉的闽西定光佛
郑自严。
可是,笔者在建阮南雅定光院进行调查的时候,庙祝却称定光
佛来自汀州,在闽西一带非常著名。而介绍过程中又夹杂七岁成佛
的故事,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见由于长耳和尚行修并不是
本地的地方神,闽北人民对其也不是特别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闽北深山中定光院里祀奉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幸运的是,在定光寺里还保留着两块碑记,从中可以获悉此定
光院大致的历史。碑记称“定光院始于何年未得确考。父老相传最
早为南雅张膺坟墓,后因定光佛显灵,始建小庙一座,供奉定光古
佛。大清咸丰元年进行第二次重建。而后香火旺盛,成为南雅主庙
之一,定光佛亦为南雅权威之佛。重建之后,迎佛仪式庄严隆重,
南雅本籍人士通为集资值事,居住南雅的福州籍民众负责戏文琐呐
彩装蜜驾。汀州籍民众负责三眼神梳,鸣锣开道。江西籍民众负责
自街到殿布帛遮蓬。一路香灯叩拜,十分壮观。”
从中可以了解到,早在咸丰之前,此定光院早已存在。但当时
只是一座小庙,在当地并没有受到特别重视。倒是咸丰元年第二次
重建之后,定光佛成为当地的权威之佛。为什么在重建之后,定光
佛突然成为当地的主神?这是十分值得思考的。从碑记中我们可以
知道,重建之后隆重的迎佛仪式是由移民到南雅的各地民众共同参
与的,其中就包括汀州籍的移民。因此,建欧南雅的定光院极有可
能是在他们的要求之下重建的。而明清时期闽西的定光古佛郑自严
已经成为福建最著名的定光佛。由于汀州民众所信仰的定光佛是闽
西的郑自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建欧南雅原有的定光佛就是闽西
的定光佛。流传下来,当地民众因此仍然认为,此定光院的定光佛
来自于闽西。
碑记中还有记载:“建国之前,每年正月初一至十六日,南雅都
会举行迎神赛佛活动。定光古佛首当其冲。迎接定光古佛规模之大,
时间之长,势闹非凡,盛况空前。建国之后,因水库建设,庙宇荒
废,神像尽毁。僧侣还俗。一九八五年在释泽福主持下,承蒙善友
信士相助,费资万多元。重建定光殿,塑造定光佛像。定光佛居中,
华光佛居左。齐天大圣居右。两侧二四诸天,排列整齐。一九九一
年元月新建大雄宝殿,塑状三宝佛像,两侧十八罗汉形象逼真,右
殿供奉观音佛,左殿供奉地藏王,前殿建成之后,定光寺又将更加
兴旺。”
可以获知,此定光院在一九八五年还经历过第三次重建。今天
在定光院的大殿里所能见到的定光佛大的塑像就是在一九八五年建
成的。此塑像与普通寺院佛像的塑像无差,只是在佛像前又摆放一
佛完,里面供奉的是儿童形象的长耳定光佛。当笔者问到后来的塑
像为什么不是儿童形象时,庙祝告诉笔者,这是由于当时建造神像
的师傅不了解情况所致,原本的定光佛形象就是佛盒里七岁长耳定
光佛。由于七岁长耳孩童形象的定光佛像依旧被保存下来,我们依
然可以获悉闽北定光佛的最初形象乃是行迹于浙江的长耳定光佛行
修。
那么,为什么在闽西和闽北会出现两位定光佛的巧合呢?笔者
认为,这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首先,无论是闽西的郑自严还是闽北的长耳和尚行修都是佛教
中典型的密僧。密教强调即身成佛,认为通过法身三密的加持,佛
的力量就会显现到自己的身上,使自己成为了佛的化身。佛有神通,
掌握此佛密法的僧人顺理成章地也有了神通。在史料的记载中,闽
西的郑自严以及闽北的长耳和尚行修都有异于常人的表现,佩展示神
奇是修密法的表现。而二者都被称为定光佛,很有可能是修同一种
密法所致。
另外,定光佛是佛教中很重要的人物。定光,梵名Dip二!kara,
音译提沮揭罗、提恒揭。《瑞应经》译曰锭光,《智度论》译曰然灯。
锭为灯之足,锭光其实就是灯光的意思。因传说中定光佛出生时身
边一切光明如灯,故其又被称为燃灯佛、锭光佛、锭光如来、然灯
如来、普光如来、灯光如来。佛经中定光佛是过去佛,即在释迩牟
尼出世之前即己成佛,且为释逸牟尼的前世说法、授记。因此定光
佛为过去佛中之最著名者,在佛教中有很大影响。鉴于定光佛在佛
教中的特殊地位,两人先后将定光佛作为其修炼的本尊,也是非常
符合常理的。
最后,宋代是福建密教特别盛行的时代。二者先后出现在唐宋
之交,同被称为定光佛的化身,极有可能是由特殊的时代背景所决
定的。
无论如何,闽西客家移民在闽北定光佛信仰的转变及兴盛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闽北原有的长耳定光佛信仰,早在咸丰
年间,基本上已经被闽西客家的定光佛信仰所同化了。在闽西移民
的影响之下,定光古佛亦为建哑南雅权威之佛。可见其对当地民众
影响之深。客家民系是勇于流动迁徙,在流动中不断壮大自己、丰
富自己的杰出代表。在闽北的表现也是如此。正如陈俱先生所说“中
华文化是在各民族、各民系的长期流动迁徙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这样的流动迁徙,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洪流,使人民的各个部分互相
交汇,互相融合。文化的总体因此也越来越丰富。”5闽北定光佛信
仰的转变正是其中最典型的折射。
作者:
黎晓铃:女,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陈俱《闽西客家外迁的两个家族》,载于《客家》2005年第4期第20页。